
《驾驶我的车》
当下生活处于激烈的变化中,既往的确定性不断受到侵蚀,为在流变中寻找生活的自主感,人类学家项飙和哲学学者王小伟进行了一次线上对谈。
项飚因“附近性”的概念为大众所熟知。王小伟则于近期出版了随笔集《日常的深处》,以技术哲学为基底,讨论人与物品与生活的关系。他们试图从哲学与人类学的交叉中寻找思想资源,来应对剧变的挑战。
💡德国马普所的段志鹏主持了本次对谈,蒋文丹对录音进行了文字整理。牛津大学的陈志峰参与了对谈。篇幅所限,文字资料整理自部分座谈内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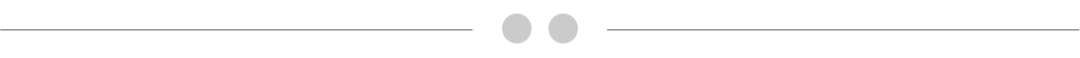
01.
宏大叙事
“有些宏大叙事的结构是固定的,僵化的,你自己的经验是没办法回视它的,而要受到它的摆布。”
王小伟:项老师一直愿意朝向公众说话,关注年轻人的遭遇、年轻人的焦虑和无意义感等生命力萎缩的情况。您谈论“附近”比较多,给人感觉排斥宏大叙事,也和宏大的理论本身保持了距离。似乎年轻人要摆脱焦虑,重获生命感不太需要大的哲学和人类学理论,而是要关注自己的“附近”。这起码是第一步?
项飙:如果我们把宏大叙事理解为一个稳定的象征性结构,一系列的牢固观念,一个是在你的经验之上、经验之外的意义的话,那当然要摆脱这个结构。这种结构是固定的,僵化的,你自己的经验是没办法回视它的,而要受到它的摆布。

《塞瑟岛之旅》
第三种宏大叙事是更具反思性,其根本是要问我们究竟在干什么?像我们所要做“共同焦虑”的人类学研究。如果没有宏大叙事,这个研究就不太成立。在这个点上,我特别希望向哲学界学习新东西。
比如李泽厚的工作,他是中国20世纪后半期一个非常重要的人物。李泽厚是宏大的,抽象的,他从美学出发,将美感、情绪、体感,跟康德、马克思等结合,提供了独特的主体性理论。
李泽厚可能是80年代影响最大的一个学者。他的影响力从社会学、人类学的角度去看是有原因的,因为李泽厚给大家提供了一个视角,这个视角有社会和政治含义。你必须有宏大叙事的视角才能理解李泽厚的思想为什么有那样的影响力。
同样的,理解整体性焦虑也需要宏大叙事。年轻人觉得不爽,我们要问是什么东西让ta感到不爽?怎么理解ta的不爽,ta怎么表达不爽。对不爽的不同表达方式分别体现了什么样的权力结构,自我认知等等。
你不断追问,最终我们需要一个潜在的宏大叙事来帮助理解。我觉得必须有个宏大叙事才能知道我们今天在历史中处于哪一刻,我们在干什么,这样才能深刻理解年轻人具体的困惑。
比方说年轻人的“不配感”,你如果只做实证的话,讲不清楚的。ta怎么会觉得不配呢?有些东西明明是自己考上的,经过很多努力,ta反而觉得自己不配。这反映了对自我存在的一个认知。
这不仅是个心理过程,这是ta对自己长期的成长经验的总结,很可能也包含了ta父母的成长经验和心态。这需要通过哲学思考把这个现象转变为一个更大的议题。

《完美的日子》
王小伟:所以您排斥的是作为意识形态的宏大叙事。因为我们没法回望,对它无能为力。第二种宏大叙事是琐碎的,是一种日常讲述习惯。第三种是反思性,历史性地,要去问我们在历史中处于什么位置。这样才能有效回应现实中具体的问题。
李泽厚所处时代的宏大背景是一个开放的,试图融入世界文明的中国。重新发现中国人的主体性是他在那样一种宏大背景下的系统性尝试。
赵汀阳是李泽厚的学生,他近来讨论比较多“后人类”问题,其实就是科技时代人的主体性流变的问题。我们正在一起写一组后人类的稿子。
他对于深度科技化时代每个人所遭遇的这种虚无感、无意义感,都感同身受。他似乎认为科技的无处不在会造成道德的崩坏。他似乎也操持一种理性人文主义的态度,热烈地希望通过弘扬理性来阻止堕落。
不过宏大叙事的哲学计划今天不时兴了,像黑格尔那样的历史哲学,包括李泽厚那样的主体性哲学可能都很难引起兴趣了。
02.
总体化焦虑
“年轻人今天的问题往往呈现为一种‘总体化焦虑’,甚至渴望让世界毁灭”
项飙:我们没有雄心去给大众提供一个宏大图景,但是我们自己脑子里是有个大的图景,这是给自己用的,帮助我们去理解具体的社会问题。无论如何我们都需要一个总体性(totality)的视角。
比方说马克思主义就通过商品的概念把所有社会关系连接在一起。卢卡奇也注重总体性的概念,认为资产阶级学说越分越细,每一个细节都是正确的,放在一起就错了,只有无产阶级才能看到全局。
总体性和总体化不一样。总体性是一种分析方式,看到多样事物之间的联系。总体化是情绪性的,把所有事情看作一团。
年轻人今天的问题往往呈现为一种“总体化焦虑”,甚至渴望让世界毁灭,觉得整个世界就是这样的不堪,就是很不公平。这种焦虑的表现很绝对化。
最后这个总体化的焦虑又变成一个既定的象征结构、象征秩序了。你也没办法回望它了,总体化焦虑还是带来了无力感,焦虑完你什么也没有干。

《酒精计划》
王小伟:您似乎有两个企图。一是朝向实践,渴望年轻人找到某种整全感,这种整全感能够导致具体的行动,提高人的生命力。另外一个可能是哲学的,是一个本体论工作。
欧陆和分析哲学家都有自己一套本体论方案。在深度科技化时代,像大卫·查莫斯这些人也会提出一些新的方案(例如比特本体论)。我不确定哲学本体论是否能帮助我们缓解焦虑,应对虚无。在本体论层面,我不知道人类学究竟要走多深,它要变成哲学吗?
项飙:总体性不是我要对世界做出一个判断,它不是一个断言(assertion),主要不是一个哲学本体论的描绘。
在人类学里,总体性是我的一个实证观察:年轻人自己在生活里面有着关于总体化的想法和说法,例如渴望世界毁灭。我觉得要对抗总体化焦虑,不是说要回到岁月静好,关注自己一亩三分就能解决的。
我想从实证角度来考察一种总体性的世界观,也就是观察年轻人他们怎么看世界的。比方说,通过对年轻人的生活经验和他们的生活意识进行民族志书写,让他看到具体的事物,并非独立存在,截然分割的,它有各种各样的丰富的联系。
比如说教育对生命力的影响。你可以把教育理解为学习知识,理解为社会驯化,理解为阿尔都塞所说的意识形态装置,理解为社会关系的再生产,理解为人的工具化,都可以。
如果把教育理解为对生命力的一种运用,问为什么今天的教育让年轻人觉得没生命力,要深挖这个问题,就会进入一种潜在的“总体性”的分析方式。
在学校里我们不仅是在学知识,老师看我的眼神是怎样的,同桌怎么对我说话,考试前的紧张,考试后的释然等等都是联系在一起的。这个联系在一起不是本体论意义上的,它指的是教育制度和环境的设置。
教育作为一个生存活动如何对我们生命力造成影响,这是我们感兴趣的。一个学生感受到的生命的萎靡包括两部分。一个是最直接的反应,比如ta们觉得累了、麻木了,这是经验基础,第二要看ta怎么处理自己的经验,这会需要用到语言、概念。

《瞬息全宇宙》
王小伟:比如说年轻人觉得痛苦来自内卷,“内卷”就是一个去解读自己生命经验的概念。内卷、焦虑,包括抑郁现在都变成了泛在概念。二十年前这些概念并不用来解读人的生命经验,内卷闻所未闻,焦虑和抑郁还是精神诊断词汇。日常生活里我们会说竞争激烈、有点紧张、有点不开心。
你觉得普遍性的,总体化焦虑和这些词汇的发明和使用,甚至是误用有关系吗?
项飙:显然是有关系的,有一种说法认为这些词汇强化了抑郁。但这些语词在这个时候出现,它本身是有意识地实践的结果。李泽厚也讲过究竟是“语言说我”还是“我说语言”。其实两边都说得通。但在当下中国语境里,我觉得要更加强调“我说语言”,强调语词的形成是人们行动和选择的结果。
王小伟:我认同这个取舍。回到我们之前的讨论,您认为有没有一种宏大的叙事作为背景,导致了年轻人选择这些词汇来去解读自己的生命体验?
项飙:任何事情都有背景,问题是怎么样去处理这个背景?
李泽厚后期有历史沉淀说,提示要在个体的主体性里面看到历史的沉淀。比方说焦虑,我们知道青年人的焦虑跟这两年的经济下行有关,但这个是短期的,焦虑也跟他的小时候成长经历有关,这是中期的,但同时也跟一些创伤通过代际无意识地传递也有关,这是长期的。
孩子那么焦虑是因为父母焦虑,父母焦虑是因为父母小时候的经历,这会无意识地传递给孩子。比如父母小时候资源缺乏,现在看到孩子的一步走错,就认为是灾难性的。
一个20岁的人自杀可能跟中国近100年的历史有关,跟昨天考试失败有关,也可能跟20年的成长经历有关。关键是我们用什么方式把这样多层、多面的背景讲出来。
王老师,你现在是以思想随笔的形式来表达,也通过公共媒体对日常生活和自己的生命经验进行总结。我感到一到生活经验,好像我们的思考就会被生活经验本身淹没,很难作为思想主体对生活经验进行重新整理。
你个人感觉到现在走出一种以生活经验为底子,但又超出它,回头能再照亮生活的思考方式吗?
王小伟:观察日常经验肯定渗透着某种哲学视角。它不是写日记,不是对自己的生活的详尽记录。它是通过特定的视角来裁切生活,然后把裁切成果再映射到自己的生命体验当中去。我一直在试图寻找自己的人格和工作统一起来的办法,杰出的工作可能都是给生命写注。
项飙:你觉得自己和身边朋友处在一个什么样的阶段?觉得找到一个这样的理想模式了吗?
王小伟:没有。青年学者一个重要主题是在学院体制内尽快锚定资源,通过职称晋升获得稳定的生活,这基本上是摆脱屈辱感的活动,很少有人能从生命体验出发做研究。
03.
夺回日常,唤起感受
“日常生活在当下生活当中被挤压、边缘化,被认为是无关紧要的……”
王小伟:在交谈中,我注意到人类学和哲学研究方法差距还是很大的。哲学不太需要实证研究,更多在尝试建构叙事。但人类学似乎很不一样,要做很多田野。我更多的是做技术现象学的工作,试图去澄清当下生活困境的宏大背景。
当代生活的宏大背景是无处不在的技术装置和伴生的技术狂信。不少人相信科技会一直进步,物质会极大丰富,幸福将不期而至。哲学家对此很谨慎。海德格尔认为技术是科学的前提,我们必须把世界看作是一个可以数学化、力学化的东西,才能把世界表征成为科学研究的对象。
他已经预见未来世界是以计算(强控制)、快速(不等待)和巨量(无个性)为突出特征的时代。所有的意义都会被剥夺掉。人和一切存在者都变成“持存”,被任意摆弄。
科技会带来一种彻底的遮蔽,人们无法想象另外的存在方式。正像孙周兴解读的那样,真正的虚无主义只有一种,那就是技术虚无主义。
在这个宏大图景里观察当下的生活,我们几乎没有办法再去理解什么是神圣的、超越的、模糊的,我们只有一种定量的、计算的、控制的生活方式,这是造成总体化焦虑的一个重要原因。一切都是权力意志,工具理性的彰显。
当代社会中,人在家庭、公司、社交生活中都感到被“挪用”,要被用来做那些ta没有热情事。而爱、亲密关系,以及艺术这种无法计划、摆弄、榨取的东西变得稀缺,或者干脆不值一提。

《伊尼舍林的报丧女妖》
项飙:你有没有想过在中国当下的情况下,怎么继续发展海德格尔的想法。
王小伟:受到海德格尔哲学和项老师有关“附近”讨论的启发,我现在特别关注生活的日常性,写了《日常的深处》。
日常生活本来是生活世界基质性的东西,它对应的是工作性的活动,当代工作已经完全被现代技术逻辑笼罩,都是高度目的化,工具化的。日常生活却是没有目的性的,不需要考虑投入产出,不需要量化管控的。它粗糙、模糊,并且带有很强的随机性和任意性。
日常生活在当下生活当中被挤压、边缘化,被认为是无关紧要的,但其中包含缓解技术独裁的解药。我想做的工作是夺回日常生活,通过日常生活把生命力充实起来。
有些事很容易操作,比如花五分钟去树林里面枯坐,养一条鱼、种一盆薄荷等等。这些在海德格尔看来可能是一种非本真的“常人”状态,但今天格外重要。
项飙:那你需要引用很多脑科学或者心理学的研究来说明你的观点吗?比如看看神经科学对在森林里无目的地坐一下会不会产生某种心理效果?你怎么去论述日常生活跟生命意义的关系?
王小伟:这是要尤其警惕的。一旦使用脑科学去理解日常生活的重要性,你就把日常生活技术化、工具化了,日常也就变成了工作,要在其中谋求效益。夺回日常是要提高人的感受性,而不是理性。
项飙:所以夺回日常的作用不是劝说,是唤起。
王小伟:是的,是要唤起人们对存在的感受,保持一种在技术性生存之外维度,获得一种适度的意义感,不至于陷入一种“消极的虚无”。
尼采经常谈论虚无,他区分了需要强意义的弱者和需要弱意义的强者。需要很强意义感的人,ta要把自己的生命工具化。
尼采说基督徒把此生看作是走向天国的步骤,这是把生命工具化了,索要一个强意义,他们都是弱者。强者有不一样的时空感,它不关注外部,不把自己的生命当作工具,强者肯定生命本身,所以只需要一个弱意义——日常或许就是一种弱意义。承认自己不卓越,接受并拥抱日常,从中找到价值感,这反倒需要更强悍的生命力。
当然我们也没法提供一个幸福人生的操作手册,一旦手册化它就又会变成一种技术——焦虑去除术。
项老师的工作其实看起来也很像一个行为艺术。比方说《把自己作为方法》,这绝对不是一本幸福生活操作手册。书里并没有直接的训诫指导,和操作步骤。它更多的是在对话构造一种指引。这本书的写作方式很像海德格尔的《乡间路上的谈话》。

《伊尼舍林的报丧女妖》
项飙:这个太有意思了,在中国传统里有这种做法吗?
王小伟:我的阅读非常有限,但似乎前现代的东西多少都保留一些神圣性、超越性,不可言说的神秘性。比方说“道”这个概念就保持着一种不可说性,因此具有诗性。
它没有办法通过说明文来澄清,只能通过诵读来体会。回到日常生活,我有个感受,似乎八九十年代中国的大学里面人们都爱谈论诗歌,演奏民谣。
今天的大学里你几乎看不见诗歌,每个人都在想着发论文。现在诗歌丧失了召集的能力。诗歌就是一种邀请性和指引性的语言,诗歌天然地拒绝清晰。
项飙:学生不写诗歌了,都在想考研这件事,在一个层面上我们可能认为ta们被工具理性占据了。但ta心里是不高兴的,是觉得压抑的,所以ta的自觉意识是有的。我们去观察这个意识,从一个启蒙理性的角度来看,这个意识活动是非理性的,所以ta没有完全被工具理性所征服。
年轻人感到的其实是生活不可测,有极大的不确定性。技术没有给ta们带来确定性。ta觉得自己的一切都是很不可测,个人处于一种不但非理性而且不合理(irrational and unreasonable)的境遇中。
这种非理性指的是从制度设计角度上是不合乎逻辑、没有效率的(irrational),比如内卷;不合理是指在伦理上是无理由的(unreasonable)。
从我们的角度来看,大家感到的不确定性就与政治经济学相关,不仅仅是因为技术造成的。它是一个社会结构造成的问题,是可以言说且必须言说的,不言说就走不出困境。
生活不可预测,如何能在不可预测的生活之流里面来做总体性分析呢?这个时候,每一刻又需要清晰语言,否则的话,难道遇到问题我们就去写一首诗吗?当然那也可能是一种办法,但我们的进路还是非常理性主义的进路。
王小伟:所以您对海德格尔式讲的回归艺术,或者我提到的回归日常这套解决方案并不完全满意。
项飙:当有人把枪拿出来的时候,你该怎么回应?在黑森林里面行走,在林中枯坐是不能回答枪口下的逼问的。你要有一种古典意义上的理性,加之再回到人本主义,这个人本主义就是早期马克思人本主义,这样或许才能解决问题。
王小伟:项老师,我隐约看到了一种世界图景的根本差异。在理性和感性之间,我们似乎有不同的偏好。
